冰岛爱尔兰两种财政调整给世人的启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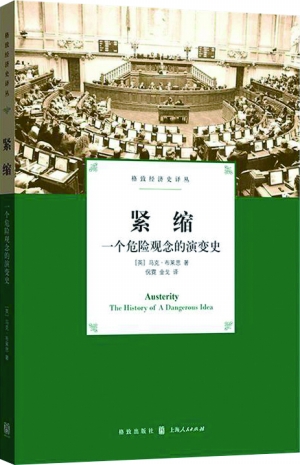
《紧缩》 一个危险观念的演变史 (英)马克·布莱思 著 倪 霓 金 戈 译 格致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读马克·布莱思《紧缩:一个危险观念的演变史》
⊙潘启雯
金融业自受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重创后,美欧政客们宣布了一轮又一轮预算削减计划,并将政府支出塑造成无妄的浪费和经济形势进一步下行的“罪魁”。在《紧缩:一个危险观念的演变史》的作者、布朗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马克·布莱思看来,这些观点和举动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问题的源头并不是政府狂妄无节制的支出,而恰恰是政府对破产银行体系的救助、再资本化和注资。这些行为将私人部门债务变成政府债务,这些债务的始作俑者偷梁换柱,让政府来承担罪名并让纳税人承担偿还责任。这种偿还责任现在甚至演变成了全球式紧缩,即采用降低国内工资与价格的政策来恢复竞争力并且平衡预算。
紧缩思想屡次回归
并演变成危险理念的根源
布莱思认为,除教学与科研外,学者更重要的另一部分职责是承担“审视政策”。通过纵横对比研究,他发现,作为一种聚焦于政府管理与市场关系的理念,紧缩的思想史不仅短暂,更苍白。紧缩的起源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的空白断层,“大萧条”后被理性的思想放逐,而它在蛰伏等待机会。在其冬眠的时间里,德国秩序经济学、美国的奥地利学派和意大利经济学家思想不断发展,最终促其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全面回归。用佛蒙特州明德学院经济学家大卫·科兰德的评价,紧缩主义是对政府功能各种“过度敏感”的思想总和,它紧紧嵌入在自由经济主义的萌芽中,成了市场失败时默认的政策选择。布莱思教授从长历史维度中研究发现,它在实际操作中是无效的,从根本上说是让穷人为富人的错误买单,全球经济存在一个重大的“集体性谬误”,这三条原因使紧缩成为一种危险理念。
在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西方各国政府为拯救全球银行体系所支出的救助与再注资成本高达3万亿到13万亿美元。由于政府为金融危机买单,因此绝大部分救助成本最终反映在政府资产负债表内,因而人们错误地认为这是一场“主权债务危机”。但实际上,这是一场精心掩饰的、不断变形的银行业危机。无论如何,当任何一家巨型银行无法运营时,只有其所属的国家能出手救助。可是,只有当一国债务占GDP比值小于40%时,这种救助才可行。如果一国的债务占GDP比重已接近90%,那么政府在救助银行的同时将不可避免地推高其国债利息。
经济学家们在讨论分配问题时常会提到一个有趣的比方——“比尔·盖茨逛酒吧”。当比尔·盖茨进入酒吧后,酒吧所有成员的平均财富大幅激增,似乎人人都成了百万富翁。事实上,酒吧里只有一个亿万富翁和一群身价数万美元或更少的普通人。紧缩对不同收入人群的政策效果截然不同,因此也面对同样的困境——在统计上正确,但实际却毫无意义。处于收入分配最底层的人群遭受的损失远大于处于收入分配最顶层的人群。
有个很奇怪的现象,似乎只有在通胀时期,人们才关注穷人的收入分配。理由是穷人更易受价格上涨的影响。然而,这最多只能算说对了一半。通胀是一种针对阶层的税收。当“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时,便会出现通胀。通胀使负债方得益于借贷方,通胀率越高,负债方应计偿还的实际债务就越低。由于通常来说负债人的数量要多于借贷人,而且借贷人是有空闲资金出借的人群。这样,借贷人将获利而负债人受损。相反,在通缩情况下,每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接受减薪以保住工作岗位)加总起来实际上是一场“零和游戏”(在消费降低的同时,对产出的需求也降低了)。说到底,这正是个“集体性谬误”。在这个过程之中,没有任何赢家。欧元区周边国家过去数年的经济表现充分证明:对紧缩的预期越高,后果则越惨烈。
布莱思教授研究中发现,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紧缩对国家是有效的,但前提是不存在“集体性谬误”。也就是说,存在一个更大而且未削减的国家,这个国家能进口削减国家的出口商品,以抵消削减的负面效应。遗憾的是,对绝大多数国家而言,现实世界并没有这么理想。不仅如此,目前,即使能解决政治上的可持续问题(“谁承担成本”),经济问题(“所有人同时削减”)也依旧会否定紧缩。
与探索“紧缩成为一种危险的理念”的三个原因相映成趣,从理论范畴转到实践领域,布莱思教授也沿着三大路径考察紧缩的实践历史。其一,20世纪20、30年代断断续续的金本位时期存在多个推行紧缩政策带来“危害”的经典案例:美国、英国、瑞典、德国、日本及法国。在这些案例中紧缩政策登峰造极,实施紧缩的国家要么失败了要么被毁灭了。这些案例清楚地告诉人们:经济并不会在“萧条和崩溃”之后“自我修复”。布莱思教授考察这些案例失败的原因并且从中总结经验,认为这些经验对当今的情形非常有价值,尤其对如今的欧元区而言。
其二,与“危害”经典案例相反,也存在如艾莱斯纳、吉瓦茨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强调的正面案例:丹麦、爱尔兰、澳大利亚和瑞典。这些案例被视为“大萧条”时期成功的扩张性紧缩。布莱思教授以这些国家的经验来分析今天的欧元区,直言即这些案例成功的条件并不是目前的欧洲所具备的,特别对“南欧五国”(即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而言。充其量,这些案例只能说明扩张性紧缩是一种特例。
其三,紧缩簇拥者的“新希望”:罗马尼亚、爱沙尼亚、保加利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REBLL联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在近年将REBLL国家视为紧缩政策的“新证据”,并将他们作为经验模式推广给西部和南部欧洲的国家。但事实,REBLL的政策执行条件及他们独特的经济与政治结构使这些国家的政策经验比20世纪80年代欧洲西部国家的经验更难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所以,完全不能证明紧缩的有效性。在某些情况下,REBLL联盟各国确实在危机中维持了汇率稳定,但代价是自愿的、大幅的通缩、对外移民及失业。他们远远不是榜样,只是再一次提醒紧缩的无效性与沉重代价。
未来或许是
“糟糕选择之外最差的选择”
澳大利亚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奎因将那些存在明显逻辑不一致问题、在实践上失败过无数次,但却仍残存至今的经济理念称为“僵尸经济学”。紧缩正是一种“僵尸经济学”,历史无数次否定,而它却一次次卷土重来。究其根本,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那个俗语——“再度举债无法真正偿债”是如此的简洁并富有吸引力;另一部分原因是政治保守主义者能利用这一理念将国家福利主义挤出政治舞台。
为此,人们看到,在这次欧洲金融危机中,政客们热情洋溢地采用紧缩政策,然而,与布莱思教授考察紧缩的思想与实践史的结果如出一辙,紧缩依旧失败了。如果欧洲的经济政策制定者是承诺“不造成任何伤害”的医生,那他们可能早被吊销“营业”执照了。如果紧缩很快将成为美国的政策咒语,那即使无视迄今为止的所有事实证据,人们依旧能预期紧缩会给美国带来巨大危害。
救助银行带来政府债务,结果是危机,而危机又带来了紧缩。即使其根源是现在的货币末日机制中的“大而难救”的银行系统,即使看起来除了“增加中央银行流动性、挤压预算和祈祷”之外,别的选择都极其有限。
难得的是,布莱思教授在最后一章中大胆推测:投资银行这种商业模式可能已行将就木。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我们在危机中损失的所有资金都浪费在了一个终究要衰退的行业里。但冰岛和爱尔兰两个小国的财政调整或许能给人们带来新的启示:冰岛让银行破产,不仅熬过了危机,还让冰岛变成了一个更富有、更公平的社会。爱尔兰救助了银行,代价是长久深陷于救助后的痛苦中。
如果冰岛给我们带来了正面经验,那么,未来在何方?照通常的设定,高度负债的社会能选择的未来极为有限。布莱思教授的思考是,走出危机的方法除了常见的“通胀”(对资本及债权人有害)、“通缩”(对劳动者及债务人有害)、“货币贬值”(长期对劳动力有害,在欧元体系下不可能)及“违约”(对所有人都有害)四种选择外,还有金融管制、在全球范围内征集税收两个新方法值得探索和尝试。可惜,因为这两个举措不会给银行什么好处,金融界不会支持。这两个方法,不妨借用丘吉尔对民主的评价:“这是现有糟糕选择之外最差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