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撑中国古代技术成就的理论是什么?

《文明的滴定》 (英)李约瑟 著 张卜天 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8月出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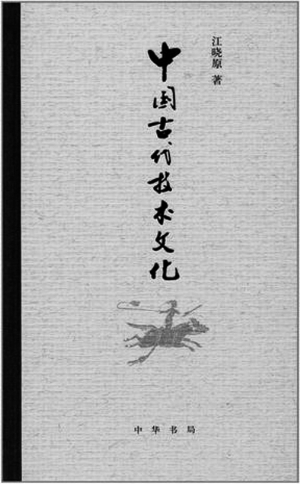
《中国古代技术文化》 江晓原 著 中华书局 2017年8月出版
——读《文明的滴定》《中国古代技术文化》
⊙林 颐
西方学界一直有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对此,科学史家江晓原在《中国古代技术文化》导言里如此说:“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以及如何评价这个问题本身的意义,都和科学的定义直接相关;而愿意使用哪一种定义,又涉及更为深层的问题,所以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议。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中国古代的技术成就,因为有目共睹,就很少争议。因此,从中国古代的技术成就出发,尝试思考这些技术成就背后的理论支撑是什么,不失为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问题。”
从这段话可看出,江晓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尝试思考这些技术成就背后的理论支撑”。而有关“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争议,自然让人联想到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长达五十余年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他那本《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煌煌十五卷,作为一篇刍议,不妨选取简明版《文明的滴定》,与江晓原这部篇幅差不多的《中国古代技术文化》,先做个简单的比较。
李约瑟强调:“虽然现代科学起源于欧洲并且只起源于欧洲,但它建立在中世纪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欧洲的。”他认为,“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尤其是印刷术、造纸术、火药和指南针,被归结为“中国的四大发明”,这些发明的传播对欧洲和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只是,四大发明是否真的像李约瑟所说的那样,引发了西方社会的大变革?是个迄今仍然争论不休的话题。江晓原为此分别写了四篇文章,一一分解。
首先说说火药。为了论证清楚这个问题,必须明确黑火药和黄火药的区别。今天通用的黄火药,起源于1771年合成的苦味酸,但是,火药在欧洲军事上的使用显然远远早于1771年。通过对中国的炼丹术、阿拉伯的“希腊火”、拜占庭的“海之火”等资料的分析对比,江晓原因此认为,“黑火药”的发明权应当归于中国,而且它的确大致符合恩格斯所说的,“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中国人的黑火药把欧洲的骑士阶层炸得粉碎,这个论断是可以成立的。
其次,说说指南针(司南)。按江晓原的说法,迄今,中国文献中出现“司南”的记载,主要有以下两条:“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韩非子·有度》)“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向南。”(《论衡·是应篇》)前者属于政治秩序概念,后者所说的“柢”包含了一段横木,应当是指南车而非指南针。最主要的是,至今无人能在不依靠现代技术的条件下做出司南。针对中国科学史上的“四大奇器”(司南、指南车、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江晓原做了一个命运列表,其中只有指南车的现代复制被公认为是真正成功的。
接着说说造纸。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优先权”的争夺上,而这涉及对“纸”的定义。对于目前发现最早的“中国古纸”——灞桥纸,学界争议很大。这种西汉麻纸表面粗糙,纤维难断,关键还在于,任何一张灞桥纸上都没有发现文字书写。现有的证据表明,中国造纸术是沿着唐朝-阿拉伯-欧洲这条路线传播的。
再就是印刷术了。大唐咸通九年(868年),王玠雕版印造的《金刚经》,被公认为中国人拥有雕版印刷发明优先权的实物证据,已成定论。韩国人疯狂争夺活字印刷发明权,这个问题好解决,虽然从李朝时代开始,朝鲜广泛采取了金属活字印刷术,但早在1485年朝鲜活字版《白氏文集》里就有活字法源自中国的明确说法。但是,活字印刷为什么在中国古代长期难以推广呢?这和汉字构造法有关。西文用字母,排版操作容易,而汉活字排版操作人必须要有较高的文化,起码他得认识这些字,而这在现实中却非常困难。所以,古腾堡的印刷术掀起了欧洲飓风。
近年来,“新四大发明”的倡议频现。江晓原认为,讨论这个问题必须考虑三个原则:一,要对中国文明或中国人生活有着广泛的影响;二,要尽量保证在世界上有着尽可能大的发明优先权(不一定要绝对“世界最早);三,有足够的科学技术含量。他据此提出的选项,包括丝绸、中医药、雕版印刷、十进制计数。备选的则有陶瓷、珠算、交子(纸币)、农历(阴阳合历)。这个名单肯定会有争议,但至少说明了中国古代的技术发明是蓬勃的,多方位的。
不过,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技术的观察范围确实广阔。在《文明的滴定》中,李约瑟还谈到了中国在马匹挽具、独轮车、水力鼓风机和钢铁冶炼等方面的成就。中国古代的天文学研究,尤其引人瞩目。李约瑟很推崇北宋苏颂和《新仪象法要》。苏颂就是“四大奇器”之一——水运仪象台的主要设计制造者。该仪器被认为是集天体观测、天象演示、计时钟表、自动报时功能于一体的精密天文仪器。李约瑟说:“时间测量是现代科学绝对不可或缺的几种工具之一。”因此,水运仪象台非常伟大。江晓原认为,水运仪象台尚未复制成功,只能被看作“神话和传说的尾巴”。以笔者之愚见,水运仪象台和司南、候风地动仪的情况不同,较之记载近乎空白的此二者,苏颂的相关描述非常详细,具备实践可行性,虽然可能由于保密的缘故,于紧要处故意模糊,造成后世复原的障碍,这个水力驱动的大型机械天文装置可以被视作中国人的智慧结晶,即使还需进一步求证。
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江晓原比较推崇《周髀算经》。他自述对《周髀算经》十几年前就下过一番苦功,给全书做了注释和白话译文。10年前,江晓原出版了一本《科学史十五讲》,其中详述了天文学上的一场旷世之争,即“混盖之争”,涉及与宇宙结构相关的许多内容。《周髀算经》便是论据之一。10年后,江晓原在《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中推出了一个惊人的假说:《周髀算经》中的宇宙学说和古代印度的宇宙学说非常相似,或许受到后者的启发。此论有待专家的深入研究。而江晓原此论所体现出的文化交流的意识,不仅看到中国的对外传播,也提醒我们注意外部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中,江晓原还有个让人关注的要点:那就是对中医药的看法。围绕对“中医无用论”的批评,江晓原主张维护中医的地位并继而推动中医的复兴。他直言,所谓“中医科不科学”其实是个认识误区。就中医理论根基即阴阳五行学说而论,当然是非科学的。但问题是,非科学,就是错的吗?该不该把一切都纳入科学的轨道?往外延伸,这也关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争论。如果说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那么,我们为什么研究科学史?
李约瑟说,假如我们把科学仅仅定义为现代科学,那么科学的确起源于文艺复兴晚期,兴起于16、17世纪的西欧,以伽利略的时代为转折点。但这与整个科学不是一回事,因为在世界各地,古代和中世纪各个民族一直在为即将耸立的大厦奠定基础。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学说包涵丰富的自然观念,也有“人定胜天”的思想,但更讲究“天人合一”,中国文明有着内在的稳定要求,发明和发现是为了使现有秩序更和谐。中国人没有西方那种旺盛的征服自然的欲望,不像欧洲人那样追求剧烈的变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变化。
对于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寻找答案。这些研究与探索,最后还是要落到我们对“科学”的认识,以及我们要形成什么样的科学观。





